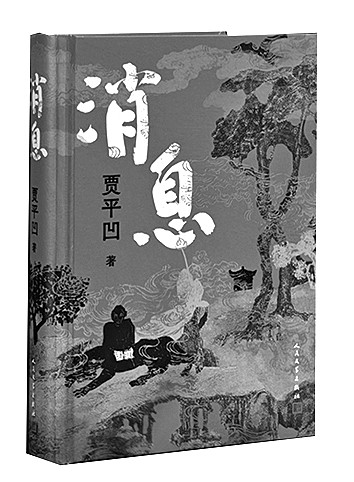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
近日,贾平凹的新作《新闻》由人民文学社出版。作品由九十多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短篇故事组成。它用神话般的想象和观察的视角,将世界自然、历史民俗、世人紧密联系起来,互相讲述生长在秦岭和华夏大地上的故事。
今天,本版邀请作家贾平凹从标题、创作、立意等方面解读他的新作。
贾平凹《新闻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
“讯息”是世界的气息
记者: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《新闻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吗?
贾平凹:作为一名作家,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几个问题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,中国文学的地位和可能性是什么?流式细胞仪面对人类的一些困境,我们的精神之路将何去何从?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可能?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人与物之间的关系,换句话说,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,还有什么可能呢? 《新闻》就是一部利用一切生物来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作品。
记者:书名《普渡众生的消息》中的“消息”是什么意思?
贾平凹:这本书出版后,有一个作家看了之后来找我谈话。他说书名应为《太溪》,因为屈原说“长长一口气掩泪,哀民生之艰辛”,苏轼说“哀惜生命短暂,羡慕长江永恒”。这样比较适合书中的内容。我认为他是对的,但我仍然喜欢这个“信息”。这本书表达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无尽生命。它表达了简洁性f 生命和自然的永恒。它是大地的呼吸,而呼吸就是空气,是从大地中迸发出来的空气。它更广泛、更实用,也适合当代人类语言的环境。
记者:小说以黄河晋陕大峡谷为开场,浩浩荡荡的大河开始了故事。还将天地、生物、古塔、树木、河流等自然意象与世俗风情、土著风情融为一体,呈现出当代的“山居意象”。如此详细的复印需要做哪些准备呢?
贾平凹: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,我的想法是尽量步行。我去的不是大城市,也不是旅游景点,而是陕西及其周边地区。周围有山是秦岭,有河是黄河。我去了农村,那是一个相当发达、先进、富裕的地方,是一个偏远、落后、贫困的地方。我想看看那里的山、河、民族。我们作家,尤其是我,在城市呆得太久了,对乡村的理解大多是过去式和概念。就像我常说的还原成语,我们只认识成语。如果一个习语被过度使用,它的原意常常会改变。要还原一个成语,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。
我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对于七十多岁的人来说,这样走着,身体很累,但精神和情感却是新奇而宏大的。一路走来,我看到了很多,但写作不是写我所看到的一切,而是写最触动我心的东西,或者说,我最爱的东西。山是山,水是水。这是我出来后看到的。山不是山,水不是水,我存在于其中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火五行如何输入土,如何摆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元素。山依然是山,水也依然是水。这是我回到城市后的想法。
记者:行走中你有什么新发现?
贾平凹:从写作的角度来说,我在寻找本土的东西,比如方言、土著风情、建筑、手工艺、美食、壁画、剪纸、雕刻、木画、歌舞等新的流行文学艺术。这里有新的认识、新的思维、新的哲学。比如我对西医的理解是“仙丹”,对科技的理解是上帝,就向我敞开了。当我们追求现代化的时候,本土的东西是新鲜的、充满活力的。它是推动现代化、继承民族传统的力量。我们寻找的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。
记者:《新闻报》这本书里有很多内容。我们的画。有bunsdock、河流、村庄、树林、驴、羊、鸡、青蛙等,这些图片和你的文字有什么关系?
贾平凹:这些年,我在散步、采风的同时,也画画、写生。这些素描也是我新的视角和另一种收藏方式。很符合我的写作审美。文学和绘画各有自己的语言。有些东西不能写,只能画,有些东西不能画,只能写。当然,有时候你不会写或画某些东西,所以你只能唱出来。如果唱歌与音调不符,就大声喊叫,或者跳舞、做手势。几年来,此类画作已超过200幅。本书只使用了其中的二十个。
记者:《昂巴里塔》似乎融合了很多传统,包括古笔记本小说的传统、古文的传统、诗歌的传统、绘画的传统,但它也是当代的。您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实现古今、不同文学艺术流派的融合?
贾平凹:我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过明清文体、文风。六十岁以后,他把目光转向中国文学和魏晋文学。他们有磅礴无限的田野,有对人生的情感和感叹,有纯真有趣的文笔。所以我思考如何营造一种混乱感和质感。这段时间我也喜欢听秦腔、蒲剧、豫剧等的曲调,在写作中也借鉴了很多。
我不想在类型方面过于具体。风格在变化,比如四川最擅长食物与材料的搭配,以及不同家居装修材料的搭配。它们看似随意搭配,却别具风味和图案,形成独特的风格。今天,与随着农林业和科技的发展,出现了许多新的水果,它们是通过不同果树杂交、嫁接形成的。当时我赞助了《好文章》杂志。我编辑出版过学术报告、所长笔记、考察笔记、书画等,只要是传达生活经验和智慧、文字有趣的。关于《新闻》这本书,我不同意给它一个具体的定义。流派,它不存在,它是“新闻”。
贾平凹画《浦西镇头》
昂文学是世间经验的真诚书写
记者:我个人认为,《新闻》虽然也写天地生灵,但也包含很多关于世事、人心的内容。
贾平凹:对,主要写人心。还有一个如何理解文学的问题。在一定程度上,它是传播世界的载体。rld经验,即自己的世界经验。在文学中,我希望能找到一些聪明的东西,一些给我启发的东西,或者非常美丽的句子,让我快乐,提高我的修养。如此这般的事情是如何处理和对待的?
记者:《新闻》里有好有坏,有因果。比如,老郑的爷爷给他的驴子治病,荒地里获得了丰收,家道兴旺。村民阮小寿一生与人为善。他不仅善待选择他香椿的孩子,而且还宽恕小偷。他活到九十五岁,成为村里最年长的人,无疾而终。
贾平凹:文学应该有一种情怀,就是对国家、对家庭、对人民、对众生的爱和大义。文学就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。 “德”是起码的道德,起码的标准,对吗?记者:很多作品都写人性的“恶”。
贾平凹:人性的“恶”我们也要写,但是要看从哪个角度去写。基本上,我们需要有一个衡量标准,并考虑积极和消极的方面。
记者:那么作家应该怎样写世界、写人心呢?
贾平凹:我本来就说写这些东西要有诚意。当你真诚地面对世界上的一切时,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如果你能体验到那件事,你就能正确地写出来。我怕你在欺骗自己。我认为写作应该以极大的诚实来对待。
记者: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,写作经历已有50多年。您现在的创作与之前的创作有何不同?
贾平凹:以前我是给几个人写的。比如有川菜、湘菜菜系、粤菜、淮扬菜,不可能每一种菜系都喜欢。吃辣的去川菜馆、湘菜馆,吃甜淡的菜馆去粤菜馆、淮扬菜馆。我的写作只适合某些人。今天,这些概念已经改变。我读了一些重要的佛经,得到了启发。所有重要的经典,一开始就记载了佛陀说法的时间、地点,以及听法的听众。让我惊奇的是,佛陀说法时,不仅有十方弟子、菩萨,还有三国六界的众生。众生,这四个字非常美丽。它激励我扩大写作的受众,探索自然世界,探讨自然和人类灵魂,而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或文字游戏。
记者:怎么有多年来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量吗?
贾平凹:答案取决于你的饥饿、不悦和善意。你的饥饿和口渴决定了你的食欲。你还有胃口,肠胃也很好,不累。你的不满意是因为你认为你以前写的可以更好,而你不想这样做。这也是自信的一种形式。
有远大的愿望,就有远大的志向。夸父要追日,精卫要填海,愚公要移山。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,但如果你有志向,你就有成功的可能。常见于一位老人死了十多天不吃不喝,还气愤不已。他在等一个人,他的孩子们,他们从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回来。但孩子们一回来就死了。我有一个亲戚,被县医院诊断为食道癌,并被诊断为食道癌。不要吞下任何东西。后来我去市医院看望他,他说不好,一出院就吃了一盘饺子。随后前往省医院进行诊断和检查。三天后他就去世了。可见人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。
我是一个纯粹的作家。正因为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上,所以写了这么多,根本就没有时间、没有心思去管什么,什么也顾不上。尤其是到了七十岁以后,生活缺乏必需品,变得淡泊名利,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。他只写,只唱,只画画。
记者:您对“新闻”有什么期待?
贾平凹:事实上,写作变得更加困难。越写越没自信,越写越紧张。 《新闻报》也是如此。文章发表后,我关注了社会ety对此的反应。对于食物,有的人吃是为了营养,有的人吃是为了味道。这本书更健康、更美味吗?应该经过检查和总结来组织我以后的写作。
贾平凹画《青蛙天物》
《光明日报》(2025年11月13日第11页)
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
近日,贾平凹的新作《新闻》由人民文学社出版。作品由九十多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短篇故事组成。它用神话般的想象和观察的视角,将世界自然、历史民俗、世人紧密联系起来,互相讲述生长在秦岭和华夏大地上的故事。
今天,本版邀请作家贾平凹从标题、创作、立意等方面解读他的新作。
贾平凹《新闻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
“讯息”是世界的气息
记者: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《新闻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吗?
贾平凹:作为一名作家,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几个问题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,中国文学的地位和可能性是什么?流式细胞仪面对人类的一些困境,我们的精神之路将何去何从?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可能?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人与物之间的关系,换句话说,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,还有什么可能呢? 《新闻》就是一部利用一切生物来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作品。
记者:书名《普渡众生的消息》中的“消息”是什么意思?
贾平凹:这本书出版后,有一个作家看了之后来找我谈话。他说书名应为《太溪》,因为屈原说“长长一口气掩泪,哀民生之艰辛”,苏轼说“哀惜生命短暂,羡慕长江永恒”。这样比较适合书中的内容。我认为他是对的,但我仍然喜欢这个“信息”。这本书表达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无尽生命。它表达了简洁性f 生命和自然的永恒。它是大地的呼吸,而呼吸就是空气,是从大地中迸发出来的空气。它更广泛、更实用,也适合当代人类语言的环境。
记者:小说以黄河晋陕大峡谷为开场,浩浩荡荡的大河开始了故事。还将天地、生物、古塔、树木、河流等自然意象与世俗风情、土著风情融为一体,呈现出当代的“山居意象”。如此详细的复印需要做哪些准备呢?
贾平凹: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,我的想法是尽量步行。我去的不是大城市,也不是旅游景点,而是陕西及其周边地区。周围有山是秦岭,有河是黄河。我去了农村,那是一个相当发达、先进、富裕的地方,是一个偏远、落后、贫困的地方。我想看看那里的山、河、民族。我们作家,尤其是我,在城市呆得太久了,对乡村的理解大多是过去式和概念。就像我常说的还原成语,我们只认识成语。如果一个习语被过度使用,它的原意常常会改变。要还原一个成语,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。
我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对于七十多岁的人来说,这样走着,身体很累,但精神和情感却是新奇而宏大的。一路走来,我看到了很多,但写作不是写我所看到的一切,而是写最触动我心的东西,或者说,我最爱的东西。山是山,水是水。这是我出来后看到的。山不是山,水不是水,我存在于其中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火五行如何输入土,如何摆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元素。山依然是山,水也依然是水。这是我回到城市后的想法。
记者:行走中你有什么新发现?
贾平凹:从写作的角度来说,我在寻找本土的东西,比如方言、土著风情、建筑、手工艺、美食、壁画、剪纸、雕刻、木画、歌舞等新的流行文学艺术。这里有新的认识、新的思维、新的哲学。比如我对西医的理解是“仙丹”,对科技的理解是上帝,就向我敞开了。当我们追求现代化的时候,本土的东西是新鲜的、充满活力的。它是推动现代化、继承民族传统的力量。我们寻找的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。
记者:《新闻报》这本书里有很多内容。我们的画。有bunsdock、河流、村庄、树林、驴、羊、鸡、青蛙等,这些图片和你的文字有什么关系?
贾平凹:这些年,我在散步、采风的同时,也画画、写生。这些素描也是我新的视角和另一种收藏方式。很符合我的写作审美。文学和绘画各有自己的语言。有些东西不能写,只能画,有些东西不能画,只能写。当然,有时候你不会写或画某些东西,所以你只能唱出来。如果唱歌与音调不符,就大声喊叫,或者跳舞、做手势。几年来,此类画作已超过200幅。本书只使用了其中的二十个。
记者:《昂巴里塔》似乎融合了很多传统,包括古笔记本小说的传统、古文的传统、诗歌的传统、绘画的传统,但它也是当代的。您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实现古今、不同文学艺术流派的融合?
贾平凹:我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过明清文体、文风。六十岁以后,他把目光转向中国文学和魏晋文学。他们有磅礴无限的田野,有对人生的情感和感叹,有纯真有趣的文笔。所以我思考如何营造一种混乱感和质感。这段时间我也喜欢听秦腔、蒲剧、豫剧等的曲调,在写作中也借鉴了很多。
我不想在类型方面过于具体。风格在变化,比如四川最擅长食物与材料的搭配,以及不同家居装修材料的搭配。它们看似随意搭配,却别具风味和图案,形成独特的风格。今天,与随着农林业和科技的发展,出现了许多新的水果,它们是通过不同果树杂交、嫁接形成的。当时我赞助了《好文章》杂志。我编辑出版过学术报告、所长笔记、考察笔记、书画等,只要是传达生活经验和智慧、文字有趣的。关于《新闻》这本书,我不同意给它一个具体的定义。流派,它不存在,它是“新闻”。
贾平凹画《浦西镇头》
昂文学是世间经验的真诚书写
记者:我个人认为,《新闻》虽然也写天地生灵,但也包含很多关于世事、人心的内容。
贾平凹:对,主要写人心。还有一个如何理解文学的问题。在一定程度上,它是传播世界的载体。rld经验,即自己的世界经验。在文学中,我希望能找到一些聪明的东西,一些给我启发的东西,或者非常美丽的句子,让我快乐,提高我的修养。如此这般的事情是如何处理和对待的?
记者:《新闻》里有好有坏,有因果。比如,老郑的爷爷给他的驴子治病,荒地里获得了丰收,家道兴旺。村民阮小寿一生与人为善。他不仅善待选择他香椿的孩子,而且还宽恕小偷。他活到九十五岁,成为村里最年长的人,无疾而终。
贾平凹:文学应该有一种情怀,就是对国家、对家庭、对人民、对众生的爱和大义。文学就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。 “德”是起码的道德,起码的标准,对吗?记者:很多作品都写人性的“恶”。
贾平凹:人性的“恶”我们也要写,但是要看从哪个角度去写。基本上,我们需要有一个衡量标准,并考虑积极和消极的方面。
记者:那么作家应该怎样写世界、写人心呢?
贾平凹:我本来就说写这些东西要有诚意。当你真诚地面对世界上的一切时,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如果你能体验到那件事,你就能正确地写出来。我怕你在欺骗自己。我认为写作应该以极大的诚实来对待。
记者: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,写作经历已有50多年。您现在的创作与之前的创作有何不同?
贾平凹:以前我是给几个人写的。比如有川菜、湘菜菜系、粤菜、淮扬菜,不可能每一种菜系都喜欢。吃辣的去川菜馆、湘菜馆,吃甜淡的菜馆去粤菜馆、淮扬菜馆。我的写作只适合某些人。今天,这些概念已经改变。我读了一些重要的佛经,得到了启发。所有重要的经典,一开始就记载了佛陀说法的时间、地点,以及听法的听众。让我惊奇的是,佛陀说法时,不仅有十方弟子、菩萨,还有三国六界的众生。众生,这四个字非常美丽。它激励我扩大写作的受众,探索自然世界,探讨自然和人类灵魂,而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或文字游戏。
记者:怎么有多年来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量吗?
贾平凹:答案取决于你的饥饿、不悦和善意。你的饥饿和口渴决定了你的食欲。你还有胃口,肠胃也很好,不累。你的不满意是因为你认为你以前写的可以更好,而你不想这样做。这也是自信的一种形式。
有远大的愿望,就有远大的志向。夸父要追日,精卫要填海,愚公要移山。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,但如果你有志向,你就有成功的可能。常见于一位老人死了十多天不吃不喝,还气愤不已。他在等一个人,他的孩子们,他们从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回来。但孩子们一回来就死了。我有一个亲戚,被县医院诊断为食道癌,并被诊断为食道癌。不要吞下任何东西。后来我去市医院看望他,他说不好,一出院就吃了一盘饺子。随后前往省医院进行诊断和检查。三天后他就去世了。可见人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。
我是一个纯粹的作家。正因为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上,所以写了这么多,根本就没有时间、没有心思去管什么,什么也顾不上。尤其是到了七十岁以后,生活缺乏必需品,变得淡泊名利,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。他只写,只唱,只画画。
记者:您对“新闻”有什么期待?
贾平凹:事实上,写作变得更加困难。越写越没自信,越写越紧张。 《新闻报》也是如此。文章发表后,我关注了社会ety对此的反应。对于食物,有的人吃是为了营养,有的人吃是为了味道。这本书更健康、更美味吗?应该经过检查和总结来组织我以后的写作。
贾平凹画《青蛙天物》
《光明日报》(2025年11月13日第11页)